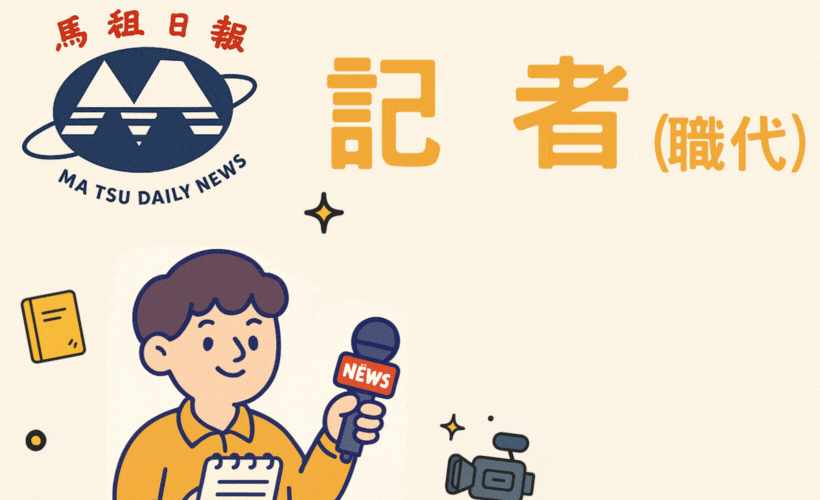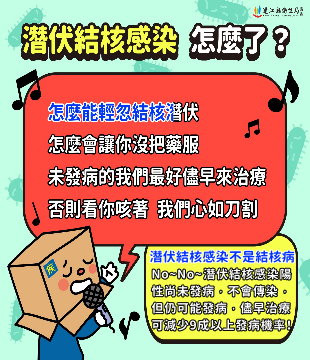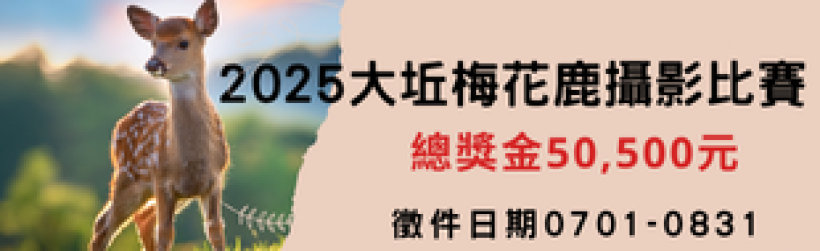前些時日,為了續修北竿鄉志,探訪北竿漁戶王國清先生,在他家門兜,看到兩只盛滿粗鹽的巨大塑料箱,鹽堆裡隱約露出兩三個魚頭,魚眼晶亮。他說:「今早才捕獲,三十幾頭!」隨即撥開鹽層,一尾一尾,閃著鱗光的白鰳魚,頭尾相間,整整齊齊掩埋在粗礪的鹽堆下。王國清說:「台北迪化街商家訂的,今年已經空運好幾百頭了!」我有點驚訝,這項已在馬祖消失多年的古老技藝,又悄悄回來了?
白鰳魚,島上稱「白力」,也有人寫成「白壢」,四季都可捕獲,但以產卵前的春天最為肥美。白力魚的刺又細又多,有一股特殊腥味,並不討喜,島人多以紅糟煨煮。昔時夏天傍晚,室內燠熱,家家戶戶搬出矮桌矮凳,就在屋外晚餐。各家吃食都差不多,番薯籤配鯷仔、帶柳,一小碟蝦油,若端出「紅糟焵白力」,大人總不忘提醒:「魚刺著細膩!」
海島人吃魚,各有講究,一般的說法是:「鰣刺、馬鮫、鯧」,與白力同個家族的鰣魚,排名第一,名氣響亮的黃魚,肉質鬆散經不起「焵」的折騰,漁人是看不上的。鰣魚罕見,偶爾捕獲一尾,料理非常慎重。50年代我念馬祖高中,有次去同學家,他爹曾是海保部隊廚師,能整一桌婚宴閩菜。那天有人送來一尾鰣刺,模樣跟白力相近,只是更厚實渾圓一些。他爹將魚身洗淨,不去鱗,全尾入瓷盤,小心翼翼罩上一層豬油網,待水滾開,立即置入竹籠清蒸。一會兒籠蓋打開,熱氣騰出,順絲切入蔥薑蒜。當時年少,囫圇食之,只記得豬油的香膩;等到年歲大了,屢次回鄉,想要尋來細細品嘗,卻再也沒有遇著。
在台灣久住,有時非常想念馬祖的海味,一般市場見不到白力魚,便往附近的漁港試試。眾裡尋它,果然在數十家喧囂的攤位中見著一尾,蜷縮一角,似乎在等待我的眷顧。老闆見我買得乾脆,好心提醒:「大哥,這魚刺很多喲!」隨後又細聲問:「你是怎麼煮的!」腦門立即浮現一句馬祖俗諺:「三月白力贏鰣刺!」一時轉不來國語,只好隨口應他:「煮紅糟啊!我們馬祖人從小吃魚,不怕刺。」
兩岸分治以前,馬祖與一水之隔的大陸長樂、連江乃至於大福州地區,共為一個生活圈。新鮮漁獲,多是以「糸孟艚」運往對岸銷售,朝發夕至,馬祖話叫「趕鮮」。然而,畢竟海象多變,魚汛不穩,多數漁產仍需就地醃漬,日曬風乾,匯集一定數量後以大船「錨纜」運到對岸,回程載運各類米糧牲畜、建材五金等民生必需,當然也會載來教書先生與鳳冠霞帔的新娘。
是以,醃漬漁產一直是島民的重要日常。在沒有冰櫃、冰箱的年代,除了依賴重鹽防腐,還因鹽粒滲入魚肉的微妙變化,使得風乾後的海味,更顯濃郁鮮美。那時,各家各戶都會便宜購入帶柳、鰮鯷、墨棗、鰃仔這類下等雜魚,「十斤魚仔三斤鹽」,密密封存陶甕,十天半月開罐,肉色轉成粉紅,馬祖人稱「鹹配(geing pui)」,揀出一尾蘸醋,可以嚥下一大碗地瓜飯。
不僅如此,昔時各島都有幾家鹹(蝦油)廠,十多只碩大陶缸內盛臭魚爛蝦,調入重鹽,加蓋後露天曝曬,任其腐化發酵。天氣好時,輪番攪拌,烈日蒸騰加上海風吹送,厚厚沉沉的臭味立時瀰漫全村,聞起來真是昏天暗地。但是說也奇怪,等到蝦油熟成,開始生火熬煮,臭味就轉成鮮味。無怪乎魚的腥味與羊的羶氣單獨都不好聞,但合在一起就是「鮮」味了。
然則,鹹配與蝦油的鹹腥,對於幹重活、出大汗,上山下海的馬祖人固然對胃,不喜的人,卻聞都不能聞。
我念馬祖初中時住校,三餐開伙十人一桌,正值發育階段,食量如狼似虎,三菜一湯的菜餚不等添第二碗飯早就盤底朝天。這時各家私帶小菜紛紛出籠,有人端出豆腐乳,有人一把花生米;東引來的同學最奢華,他們帶的是軍品──豬肉罐頭。那時與我同桌的一位學長,來自白犬島,三代捕魚;只見學長悠悠旋開玻璃罐,挑出一尾滴著鹹滷的鯷仔,正待送入口中,坐在鄰桌、台灣來的女老師倏地衝出,捏鼻大嚷:「什麼東西啊?臭死了!拿走!拿走!」
國軍來了之後,兩岸對峙,海面不時火網交加,魚獲不再運銷大陸,而是轉向遙遠的台灣。有好幾年時間,島上仍處無電狀態,除了冰船駛到東引收購新鮮黃魚,其他如蝦皮、丁香、鯷魚、帶魚、鰻魚……都以鹽漬保存,其中最大宗的即是白力魚。此其時也,適有香港商家嗅到馬祖鹹味,委託台灣代理商到島上收購。從此,白力魚躍上龍門,真個鹹魚翻身,名字也升格為雅致的「霉香力魚」。
霉香力魚做工繁複,民間土法煉鋼的「鹹配」對付不了。50年代初期,山隴老村長陳豐年先生看到商機,請了一位退役老兵當師傅。老兵姓李,廣東人,戴一副酒瓶底似的深度近視眼鏡,他要求漁民用「延繩釣」魚法,一鈎一餌釣白力魚,這比網撈更能保持魚身與鱗片的完整,尾尾碩大肥美,賣相好,價錢也高。
老李將白力魚洗淨,拆下門板當工作檯,粗鹽像座小山堆在檯上。他取一截上粗下細的木棍直入魚鰓,攪和一下拉出肚腸,再從兩側鰓口塞入粗鹽,夯實後移到巨大的木櫎裡,一尾一尾緊密排列,層層鋪鹽,有若堆疊一堵厚實的石牆。
在重鹽內外夾擊之下,新鮮魚體逐漸脫水發酵,櫎底滲出汗津津的滷汁。一星期後,魚鱗已呈半透明,脊背轉硬,老李取出軟中帶硬的鹹魚,洗淨殘鹽,攤在竹箳上曝曬,一尾尾齜牙咧嘴,狀甚可怖,卻嚇不走附近虎視眈眈、幾近瘋狂的貓群。
老李的工法不久傳遍各島,紛紛成立所謂「漁產加工合作社」,有公營也有私醃,木櫎難覓,就砌水泥池取代,甚至搭建竹寮,四面圍上廢棄的漁網,防蠅也防貓。外銷之餘,也進入島上的土產店,阿兵哥退役返鄉,背包裡除了高粱酒,還多了幾尾霉香力魚。
有一回,南竿山隴最大雜貨店「品樂」商行,跟白犬島漁家訂五十斤霉香力魚,取貨時候到了,被颱風耽擱,兩邊都忘了此事。三年後某日,漁家突然發現屋角這批陳貨,通知「品樂」領回。老闆看魚身都已乾酥,魚肉灰黑捏之即碎,便隨意棄於店外。不想這天台灣來了勞軍團,其中一名西裝男子,聞聞嗅嗅尋到店前,捧起一尾,老闆看難得有人要,隨便賣了。第二天,一輛吉普車駛到店前,還是昨天那位男子,把剩下的乾酥鹹魚整籮筐帶回台灣。
不久,食慣「紅糟焵白力」與粗獷「鹹配」的島民,也漸漸嗅出鹹臭魚乾裡細緻的霉香。偶爾購得一尾,泡水去鹽後油炸糖醋,或清蒸豆腐五花肉,或白煮配稀飯,撕一綹嚼之,稀哩呼嚕,吃得耳根都紅了。
我一位同學任教馬祖高中,有一年隨漁撈科搭實習船到日本長崎,大海行舟,預料是一段艱辛航程。臨行前,包裡塞了一小罐糖醋霉香魚鯗。果然,三天兩夜的顛簸,連膽汁都嘔出;這時,魚鯗派上用場,連吞兩碗乾飯,又生出對抗風浪的力氣。大陸作家阿城說,他壯遊四方,各式洋餐吃膩了,只要嚼過一根榨菜,所有味道都回來了。看來我們馬祖人,出門在外,要能身心安頓,行囊裡少不得「鹹」這一味的!
然而,白力魚的黃金時光大約僅維持十年左右,因為大陸漁船的強悍壓境(噸位大、數量多),因為軍管戒嚴的嚴格管制(限制出海時間、漁場),內憂外患使得漁獲大減;即便曾經多到「黃瓜打倒豆腐店」,屢屢傳出一夜致富的東引黃魚,也落至一尾野生黃魚也難以見著的悲哀境地。
這幾年馬祖旅遊正夯,新冠疫情肆虐之前,往返台馬的航班幾乎班班客滿,大家都來看夢幻藍眼淚,都來看沒有漁船的漁村。以前醃漬魚獲的鹽館,現在是學校、便利超商;以前如影隨形的鹹魚氣味,現在傳出星巴克的咖啡香。我始終以為,作為一個海島長大、從小吃魚的馬祖人,如果有一天吃不到海魚,聞不到鹹味,那將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
媽祖保佑,幸而各島還有零星幾艘漁船,他們沒有忘記祖先的行業;幸而還有王國清先生,承繼老李的醃漬技藝,為島嶼保留最後的鹹味。
2022-01-13聯合報聯合副刊【文學台灣:離島-馬祖篇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