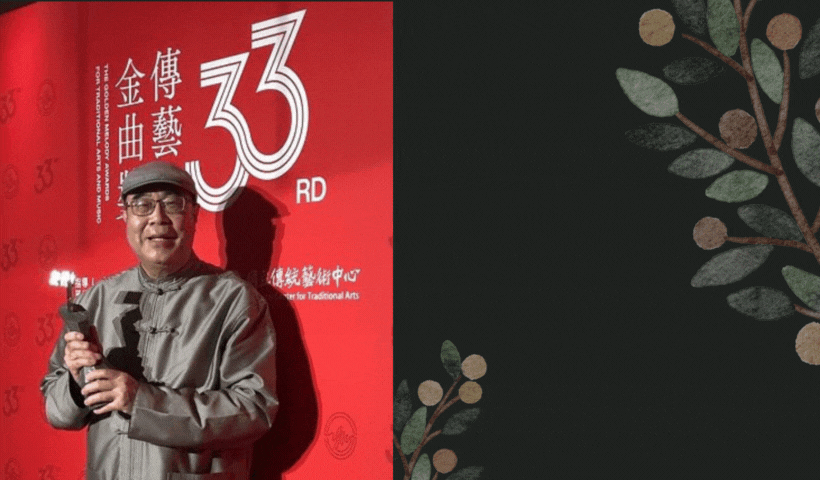如同許多優秀導演喜歡翻拍著名作家的作品,將之影像化,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Tarr Béla)也將他喜愛的作家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的作品改編成電影,而拉斯洛正是今年(202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由於意識形態與政治氛圍所致,東歐的導演常以拍攝紀錄片開始,之後才轉為劇情電影。
談貝拉塔爾三部電影《都靈之馬》、《鯨魚馬戲團》、《撒旦探戈》之前,先從二零一五年的《索爾之子》說起。由於很久沒有看到令我覺得感動的影片,這部匈牙利電影令人驚豔,當然也是拜其獲得當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之賜而眾所矚目。《索爾之子》的導演曾經做過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的助導,也是我接觸這位神話般傳說中的影像作者貝拉塔爾的起源。無獨有偶,中國大陸青年導演胡波二零一八年的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在風格與內涵上也與貝拉塔爾作品神似。匈牙利是歐洲唯一將姓氏置於名字之前的民族,與東方民族相同,彼此間歷史與文化上的連結,值得瞭解。
我的貝拉塔爾經驗始自其最後一部電影二零一一年的《都靈之馬》。且不說故事背景為眾所皆知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為馬哭泣而後瘋狂的傳聞,這部封鏡之作反而可以成為欲觀其堂奧的入門電影。黑白顆粒的攝影畫面,嚴謹的構圖,極簡且精巧設計的長鏡頭,充分表現出東歐鄉村荒涼寂靜的況味。電影文本無劇情的劇情結構也有著典型的貝拉塔爾作品特色,農莊裡的父女二人無來處亦無去處,他們在每週的六個工作日中,每日起床穿衣,在戶外狂風怒號中水井打水,三餐吃烤馬鈴薯,餵馬,駕馬車工作,上床睡覺,日復一日,永不終止。唯一打破此時間循環的是來買酒的鄰居,他對人生侃侃而談,令人覺得嚴肅中又有著突梯荒謬的意味。而後是路過農舍來取水的吉普賽家族,看似與父女兩人將起衝突,卻又嘎然而止,然後上馬揚長他去,也隱藏了電影結局中父女倆離鄉而去卻又突然回返的伏筆。
二零零零年的《鯨魚馬戲團》,一部所謂「奇觀┘電影。馬戲團是電影中常見的素材,與觀影經驗初始動機雷同,觀眾買票進場,總希望能看到之前沒見過的奇觀以值回票價。鯨魚馬戲團複製了此經驗,但也解構了它。在東歐的政治氛圍裡,導演可以如馬戲團團主一般任意包裝鯨魚的軀體,並將之神秘化,掩蓋在許許多多不可知中。而鯨魚軀體的巨大樣態本身就是一個驚嘆號,一則難以解說的神奇。文學與藝術史上所謂的晦澀與不可解等等的批判,常是此情境下的產物。但在電影結束時導演解構了它,在一場暴動中鯨魚的神秘面紗被撕毀,巨大而無辜的軀體暴露在廣場的陽光下,成為一則奄奄一息的傳奇。
最後談一九九四年的《撒旦探戈》,這是貝拉塔爾的成名之作,也是影史上難以跨越的標竿。僅是超過七小時的片長就令許多觀眾望之卻步,網路上甚至還可見到九小時的版本。只是換個角度而言,觀賞藝術品時若只是覺得痛苦而無法領略其美感所帶來的愉悅,觀賞者也需反躬自省吧。這部由拉斯洛成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描述二十世紀匈牙利共黨執政晚期,農村的頹敗荒涼令人窒息,於是離開農村便成農民的想望。但離開農村困難重重,農民遂將之轉化為等待救世主的期盼,而結果自然落空一再失望。拉斯洛的文學作品以糾結的長句著稱,貝拉塔爾將其轉換為影像時需考慮文字的質地與其節奏韻律。很難得的是他完成了此一艱鉅任務,而且如同其他優秀導演,使電影作品本身也成為藝術品。其中有許多畫面與場景都已經成為經典,影響了世界各地電影人的創作方式與對電影的思考模式。
無論以文字或是影像,創作者的觀念思維與觀看視角,以及表現的材料與筆觸,才是作品優秀與否的關鍵。至於一部電影是否應有所謂適當長度,則需視內容而定,好品質的藝術作品也會吸引適合與潛在的觀眾。
馬戲/文與圖:謝昭華
- 2025-10-27


圖一、圖二:小鎮與農漁村的日常,是貝拉塔爾電影故事的常見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