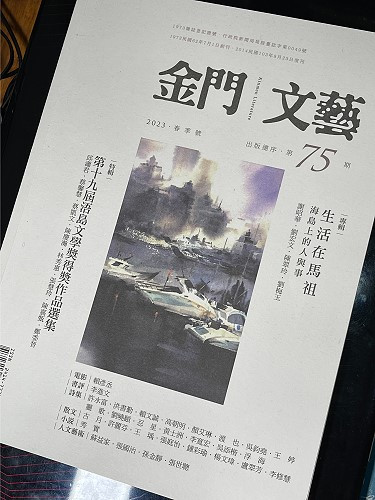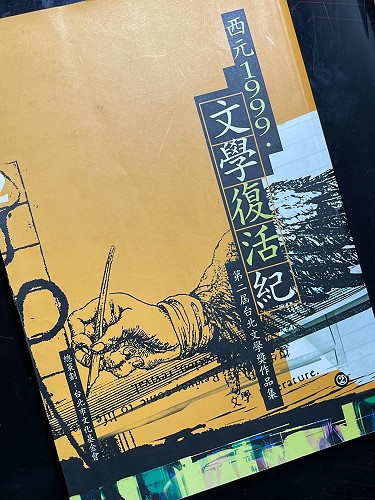文學史上早慧的作家很多,遠的不說,小說家張愛玲十八歲時寫下一篇膾炙人口的〈天才夢〉,以童詩知名的詩人楊喚十七歲時出版詩集《風景》,在此年齡時我還在英數理化的公式堆裡奮戰。
關於寫作最早的記憶是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課,曹原彰老師給了我們一個作文題目〈過新年〉。記得那時寫了除夕夜晚上姊姊鬧彆扭躲在二樓房間裡不來吃團圓飯而惹父母親生氣的故事,老師的評語是這篇作文像一篇散文。國三時的班導曹木佃老師也送過一本書做為段考獎品,書名是《文學欣賞的新途徑》,而他自己本科是數學老師。高中一年級,剛從師大國文系畢業回島上教書的陳秀蘭老師在作文課時要我們寫一首給家鄉的新詩做為課堂作業,這些都是未來寫作的養分。
大學時期永無休止披星戴月的醫學專業課程,缺乏心靈上的啟發。唯一尚存記憶中的是在大三的大體解剖實驗課程中,當我們揮汗埋首大體老師的血管神經叢裡找尋出路時,校長帶了一位白髮飄逸的長輩來到實驗室,並為他解說。後來得知,這位長輩是小說家朱西甯。而也是在解剖實驗室裡我迷失了心靈的方向,對於生命的奧秘與死亡覺得迷惘,並開始閱讀中西方哲學史,有些同學則開始接觸宗教典籍。
回到小島之後只有在週末不值急診班的夜晚,才得空閒喘息寫下一行行詩句,裝入信封,投給馬報雲台山副刊以及台灣三大詩刊:藍星、創世紀與笠詩刊。雖然身居小島一隅,藉著不斷拓展寫作的題裁,一首關於外籍移工的詩作〈班吉在染坊〉獲得聯合報新詩獎已是一九九二年的事了,那年同期獲獎的還有散文詩與網路詩名家蘇紹連〈小孩與昆蟲的對話〉與剛從馬祖退伍的方群〈北竿島組曲〉。我帶著沉重的獎座搭乘軍艦在船艙裡此起彼落的嘔吐聲中從基隆搖搖晃晃回到海島,接著每天如常為病患看診與值夜間急診班,同期獲獎的幾位小說獎得主如今幾乎都已經停筆不再寫作並發表新作品了。其實這是文學獎的常態,許多年輕作家參加文學獎只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才華,當獲得肯定之後,擺在眼前的是繼續孤獨而前途未明的創作之路,還是另尋他路謀生,這只有自己可以決定,無人可以置喙。很多文藝創作者都只是週末作家,與現實妥協,而且大多數人最終仍永遠放棄了創作。在一九九九年以〈狙擊〉一詩獲頒中國時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之後,理應是創作力最強的高峰,卻因昔日承擔重責的軍醫完全退出離島醫療的大環境下,日漸沉重的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雙重壓力,我幾乎完全停止寫作。那年的新詩首獎得主是廖偉棠〈一個無名氏的愛與死之歌〉,他已是享譽國內外的重要詩人與作家。
二零一三年接受幼獅文藝月刊邀約擔任專欄作者,也就是前年出版的《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中大部分文章的來源。二零一四年參與中國時報副刊老字號專欄三少四壯集每週供稿,此過程我在後來結集的散文集《島居》後記中敘及,也很難再回憶那一年風雨兼程每週交稿的專欄作者日子是如何度過的。
之後金門文藝總編來訊相邀,開始接觸金門作家作品。欽羨金門文風之盛,作家與作品繁多,公私資源都鼎力支持。二零二零年再參與金馬文藝中文與越南文互譯專輯《島嶼之外》,開始較密集接觸金門作家群,漸瞭解金門日報副刊與金門作家互動狀況,更覺得相較於已經開始國際化的金門文學,同屬姊妹島的馬祖文學腳步更應加快進程了。
在寫作的漫漫長路上,很多馬祖寫作者年輕時便開始發表作品,才華橫溢,但能夠克服現實環境的種種壓力持續創作才會有豐美果實。祈願所有寫作者可以在自己書桌上各闢蹊徑,開出獨特的奇花異草,留下這一代人真實的心靈面貌。
早慧/謝昭華
- 2024-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