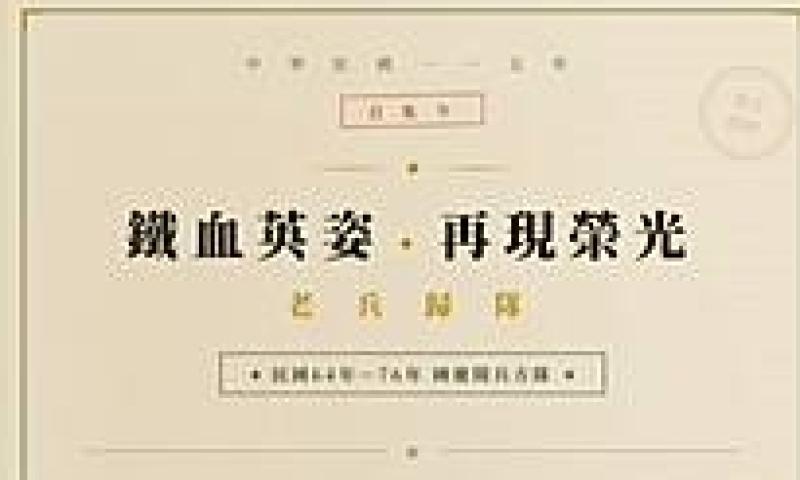第二屆馬祖國際藝術島的檢討會在日前落幕,方向與第一屆其實無太大的落差,如何擴大地參與?如何形成行政體系的支持?如何讓藝術島觀光成為一個生態系?若去年大部分都提過,可見檢討與行動之間,並不劃上等號。
兩年一度的馬祖心情記事或是馬祖國際藝術島,基本上可說是一種成果驗收,更重要的是這兩年間平日的積累得宜,才有可能讓成果得以豐厚。身為漁業專業的馬祖人,有看過在魚汛來臨之前,能夠不補好網、修好船、備妥人力、鎖定方向和位置,鍛鍊強健體魄與賣售通路,就期待能夠捕獲大量的魚貨致富的嗎?擁有漁人智慧的馬祖人,應該心知肚明。
如果都知道每年活動來臨時,一切的準備都很匆促,跨部會的整合永遠充滿著空隙,怎麼就不能從每一次的檢討會後,修整成實際的工作方針,從「地方經費」開始支應,或另覓財源,從小型活動開始跨部會合作。不能總是等每年中央的經費核定後,標案過了,第一期款下來了,通常都已經是開幕前的幾個月了,才開始所有的行動。結果就是年復一年,藝術家製作作品時間太短,藝術家在地的浸潤或攪動不夠,行銷期程過短,與在地商家導遊的對接不夠密切,進入到教育體系的教案資訊不足、餐飲民宿產業無法齊頭並進共同獲利。
而這正就是魚汛來臨前,什麼都不準備的結果。
這樣具有全國性甚至世界性的指標型活動,責任絕不會只在來自中央的文總、外來的策劃單位與行銷公司需要承擔,地方政府官員、立委、議員、各局處主管,甚至所有的在地社群媒體,你們才是決定馬祖國際藝術島是否可以走完十年,並對島上帶來改變的關鍵人物,因為您們才是人民一票票投出來,在情感與法源上,被寄予眾望的地方父母官。
疫情過後,小三通的開啟,馬祖的執政團隊,積極遊走兩岸,希望不管是台灣或是北京,都期待兩邊政府能對馬祖這個邊陲多所關注,不管是挹注資源、或是增加遊客量、物產銷售量,我想也是馬祖人民心之所向。但是,文化是很容易被清洗或是代理的,一首萬妮達的福州語歌《WAIYA》的流量,就可以抵藝術島所有影片輸出的流量,傳播速率甚至更快更高。未來若對福州表演藝術的交流更廣,大手筆投資的閩劇、具時尚元素福州語歌曲、更多類型的酒類與產品的輸入。看似更快、更有效、更有量體的文化消費行為引入,將快速的將馬祖累積多年的文化底蘊,一舉沖刷殆盡。面對台灣來的藝術如是,面對福州語本源的中國更如是。馬祖國際藝術島所辛苦想要建立的「足以與世界對話的馬祖主體性」,若在「成效是否立竿見影的考量下」,所有價值將付之厥如。
馬祖國際藝術島所邀請來的海內外藝術家們,無不以馬祖的生活、地景、歷史,作為創作的源頭。用作品帶來反思,帶居民走入禁區,打開黑暗與軍事的邊界,打開恐懼與禁忌。多少的展場,是在馬祖生活了一輩子的居民,都沒有去過的地方,比如北竿的軍魂電廠。就是這樣活化廢棄的空間,不只回望歷史的痕跡,更是資源再生,只要被當成廢棄據點、垃圾、生活用品(衣服、漁具、酒瓶、瓦片、砲彈)得以資源再利用,用想像突破限制,轉化思維便會為島嶼帶來源源不絕的生機。
島民有許多生活智慧與文化底蘊,需要平日就有人們收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系統的對接到策展團隊跟藝術家的手中,讓藝術家們經過島嶼生活的洗禮,文化的浸潤,與島民共同攜手耕耘,才能開出美麗的花朵。我們需要類似像大溪木藝博物館的「街角館」或「借問站」,將私人單位賦予公家使命,鼓勵優秀商家或社協,成為地方的文化凝聚點,輸出點,在平日即可成為馬祖文化的窗口。
在藝術島前中後期,設立特派員制度,走訪藝術品設點的位置,進行作品側拍的輸出,也採集在地居民跟旅客的觀點。島上有如此多優秀的攝影師導遊與自媒體創作者,像周小馬、掐米、東引蔡欣如等這樣具媒體流量的KOL,絕對勝任有餘,甚至讓馬高與海大的學生,在教育現場用專題的方式進行,讓青年的視角得以被輸出。
馬祖國際藝術島因著「國際」二字,要避免自嗨的行為,一定要有多重的「聯外道路」,要讓島上閉鎖的空間徹底流通。重用島上的外語人才,尤其是從台灣來此工作或婚配的人們,還有各國的新住民,他們因著更了解馬祖生態,都是將資訊帶回原生地的最好行銷人才。只要主辦單位能提供有助推廣及流通的內容(雙語或多語更好),借重個人的社群影響力,將會展現一個驚人的網絡。
藝術品跟馬祖一樣,都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地方。這兩者之間擁有許多的共通點:相對於主流它聲量較小,相對於都市它不易到達,它有不一般的過往需要被解釋與理解,它有自己的語言需要用心傾聽。但相同的是,它們都需要「交通」的輔助,讓人可以往那裏去。只要有人願意搭橋,有人願意鋪路有人願意成為河中的石子或擺渡人,每一個奉獻己力,都會成為外地人更願意來到馬祖的奉獻者。「交通」意味著有人願意往來接駁,願意運送消息與物資,願意開放,願意溝通,願意合作,願意為馬祖打造通往彼此與世界的道路。
馬祖跟藝術一樣,只要「交通」改善,對世人來說便不再遙不可及。
在下一季魚汛來臨之前,我們如何做好準備 文/謝淑靖
- 2023-11-26

圖:曹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