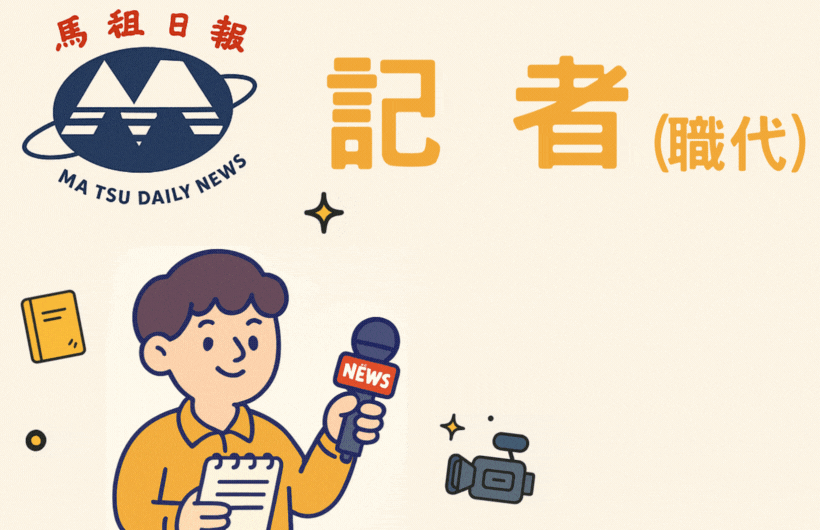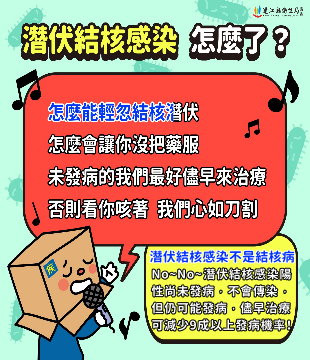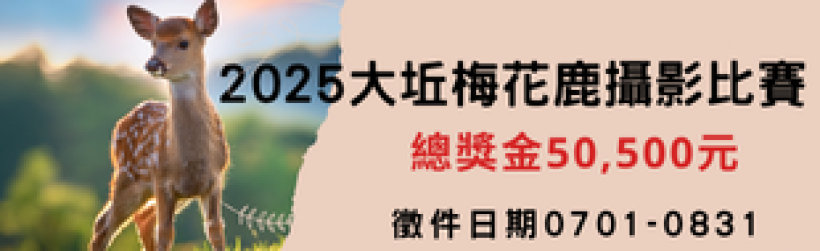(一)麻將
梅花釵不是婦女戴的髮簪,而是人名,五零年代在北竿無人不曉。
梅花釵生得高大體面,他不是橋仔人,卻長年住在橋仔。夏天他穿襯衫長褲,冬天則是大衣圍巾,比起一般漁民的短褲、汗衫與破棉襖,他的穿著講究多了。那時他經常往來於橋仔、塘岐,走著走著,軍車駛過看到,都會自動載他一程。老一輩北竿人都說梅花釵「有身分、有頭面」,年輕時曾經是「骹遛仔(遊手好閒)」;然而,也有一些人在他背後指指點點,不時冒出「土匪」、「流亡人」等字眼。
梅花釵有時不經意聽到,總是笑笑,從不辯解也不追究,以至於鄉里人都覺得他神祕、嚴肅,特別在不說話的時候,隱隱透出一股歷盡滄桑的江湖味。他有妻女在南竿,卻隻身一人住在橋仔,沒有人敢去探問。
有一次,梅花釵跟友人在塘岐艋寮打麻將。開打沒幾圈,突然衝進幾個警員,喝令他們不要動,連人帶牌押到派出所。當時島上禁賭,牌九、牽猴(賭骰子)、拍麻雀一律禁絕,公務員抓到立刻開革,民眾罰款、關禁閉。「梅花釵」被罰六百元,那可不是小數目,民國50年代,公務員月薪不過六、七百元。
梅花釵捺過手印,漫不經心地踱到到隔壁所長室。所長姓姚,一看是「梅花釵」立刻迎出來。
梅花釵面帶笑容,緩緩地說:「你欲罰我錢?」
姚所長:「釵釵叔,我也沒法的,政務大隊總款(這樣)規定。」
梅花釵:「總款吧!你現在食公家飯,我也莫為難你。你幫我繳這六百元,再借我四百,湊成一千,如何?」
姚所長:「釵釵叔,你莫講笑!」
梅花釵收起笑容,兩眼直視姚所長:「我是講真的。」
姚所長心裡一凜,立刻改口:「釵釵叔,此事就到這裡,你走吧!」
梅花釵領了另三人,揚長而去。
(二)鹹滷
梅花釵讀書名叫林芝芳,小名釵釵,民國七年出生在長樂梅花鎮。他父親與許多梅花漁人一樣,從農曆九月開始,每年都駛船到北竿橋仔,打楸掛網捕蝦皮,一直到隔年端午過後,才會回到梅花。
民國初年,連江、長樂一帶漁村,醫療落後,生死大事多靠神鬼定奪。釵釵上有一兄一姐,皆不幸夭折。鄉人相信,孩子若未及長大,其後出生的稱「罕仔」,也不好養。男孩要取命格較輕的女名,戴耳墜,才不致被陰鬼奪去。
釵釵出生那年,母親尚在連續喪子的悲痛中,幾近崩潰,已經無力哺養這個初生嬰兒。於是,父親只得從北竿返回,在梅花購置一艘「艋艚」,雇了五個夥計,魚汛雖無外頭山好,至少就近照顧「罕仔」,保住林氏一門香火。
釵釵逐漸長大,父母因兄姊逝去的愧疚,對他倍加呵護。他從小喜交朋友,好出頭,讀了三年私塾,能識字、打算盤,特別嚮往《三國演義》、《封神榜》、《兒女英雄傳》的俠義世界。
蝦皮季節一到,父親的艋寮每天都要「煠(汆燙)蝦鮮」,新鮮的蝦皮鹽煮後曬成乾蝦米。煠蝦鮮的鹽水滋味鮮美,反覆煮幾輪,湯汁收濃,變成赭紅色的「鹹滷」。左右鄰居聞香而來,跟艋寮主人討一大碗公回去,可直接沾豆腐、油條配番薯飯,也可醃帶魚、蝦蛄,那是鮮香無比的至美之味。
因為需求者眾,父親便讓十二歲的釵釵分鹹滷。他持一把鐵瓢,有模有樣,一邊喝斥大家排隊,一邊往桶裡掏鹹滷,一家一碗,直到分完為止。那時,有個八、九歲的女孩,持一空碗,好不容易輪到她,鹹滷已經見底,女孩幾乎哭出來。釵釵知道她住上村,名喚「碧霞」,父親早亡,一家五、六口靠寡母幫艋寮挑水過活。釵釵進屋與母親商量,把自家留下的鹹滷分一碗給她,隨手抓一把鹹帶柳、兩尾風乾帶魚,讓女孩攜回。
還有一次,有位高個男孩,人稱「懸哥」,仗著是他們家遠親,分過一輪後,又持碗再來。釵釵怒問:「你伓是分過了?怎講復來(怎麼又來)?」不等懸哥回話,一把奪過碗公,扔在地上,嘩啦一聲裂成碎片。懸哥一把揪住釵釵,兩人扭打,他父親聞聲奔出,看明白之後,說了句:「做歹快一時,做好食一世!」回屋拿只碗公盛滿鹹滷,交給氣呼呼的懸哥,賠不是讓他回家。
釵釵十五歲已有大人模樣,喉結突出,唇上一抹青髭,父親便讓他登船,協助拉網,從蝦鮮堆中挑出銀亮的帶魚、掙扎的海鰻,還有尾巴帶毒刺、狀若面盆的魟魚。颳風勃暴不出海,父親教他織網、結繩、製斗、做楸。
他那時年輕氣盛,也會跟狐群狗黨像一群蒼蠅,在外飲酒冶遊,尋釁滋事。可能是與生俱來,也可能是閱讀章回小說的潛移默化;少年時,在老家分鹹滷展露的脾性,一直延續到後來的交遊與處世的判斷中。尤其是海上佈網、漁鹽買賣、難免利益瓜葛,紛爭迭起。鄉里都知道釵釵這號人物,經他出面,事情便頭尾分明,梳理出當事雙方都可接納的選擇。
(三)土匪
民國三十年前後,紅軍起義的風潮在鄉間鬧得如火如荼,日本仔更從海陸夾擊;土匪、偽軍、叛軍,你來我往,各類消息一日數變,陸地海上皆不得安寧。釵釵父親擔心艋艚被劫,索性撤回漁網,讓五名夥計回家,靜待局勢明朗。
那時,釵釵經常在半暝三更,特別是雲霧瀰漫的凌晨,萬籟俱寂,他會聽到船櫓拖過石板路的「嘎嘎」聲響,經常有意無意在他家門口盤桓一陣。他知道,是那批狐群狗黨喚他出海的暗號。他們以保安為名組織船隊,桅杆時而掛太陽旗、時而掛五星旗,有時也會升起南京政府的黃旗。他們聲稱「做餉」強行收稅,也打劫外國貨輪與本地商船;他們需要軍火、糧草與養家活口的銀元。
釵釵沒有加入鄉里人稱「土匪」的海上劫掠。他那時新婚,父親說梅花局勢險峻,他們家有艋艚與艋寮,被劃歸地主資本家,百年大厝遲早會被鬥爭充公。父親讓釵釵去外頭山,他說:「那邊無日本仔騷擾,也無紅軍威脅,更可逃避拉夫徵兵的風險。」他已年邁,要釵釵往北竿投靠族親,「做艋、討小海」,掙碗飯總是有的。
民國三十二年,釵釵攜妻子與襁褓中的女兒,落腳橋仔。他很快在鄭水哥的源昇號當上夥計,夏天醃鰮鯷,冬天醃帶魚,錨纜載到泉州、福州、溫州。船行海上,為求順遂無阻,不免要向海上勢力繳納「餉錢」。有時,他也受雇「做大艋」的漁家,老本行打蝦皮,生活雖然艱難,朝來夕去,日子還算平順。
如此三年,海那邊突然傳出日本戰敗的消息,駐在坂里的幾個日本兵倉皇搭小艇離去。釵釵以為太平日子近了,不久就可回梅花老家。那天,與往常一樣,錨纜盛滿蝦皮、鹹魚,還有三桶海鹽藏在艙底,桶內都是海鹽包覆的鴉片土。船從橋仔大澳開航,剛過進嶼,一艘鐵殼船靠近;不想,跳上船收餉錢的卻是多年不見的兒時玩伴,名喚「闊嘴」。闊嘴說,他現在任游擊隊小隊長,突擊紅軍,也會潛入梅花探消息、收情報。闊嘴還說:「你老家已被充公,搬入十幾戶人家,每天雞飛狗跳,一旦生火煮飯,滿屋子烏煙瘴氣。」又說:「你爹娘住在堂屋旁的僻舍,是生是死我亦不知!」
釵釵記得那房僻舍,原是堆放漁具的雜間,他曾在那裏分鹹滷給鄰居,還和懸哥打了一架。他忽然記起,多年以前,那個濃霧瀰漫的深夜,船櫓拖過他家門口,迴盪在石板路上的嘎嘎聲響。
錨纜返回橋仔後,釵釵即告別水哥的源昇號。他把妻女送到南竿,託友人照顧,隨即登上闊嘴的鐵殼船,加入游擊隊。
北竿故事集之19/梅花釵(上) 文/劉宏文
- 2022-05-22

▲橋仔村姜伙生先生講古:梅花釵。

▲梅花人留下的漁寮,竹筴為牆,屋頂覆蓋的芒草已被塑膠布取代。(阮義忠攝影1979)。

▲橋仔村1979。(阮義忠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