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馬祖服役,運氣不錯,分發到馬祖地區最大的軍醫院當醫官,在軍官宿舍裡有自己的書桌與書架,戒嚴時期,在外島當預官一年只能返台探親一次,除了早晚點名看診及偶爾出操野戰訓練,其實閒置時間非常多,沒有什麼值得操心牽掛的事,或必須煩惱耗費大腦精力的任務,這一年又九個月完完整整的日子,整天看書、看海、看雲,真是一生很難再有的享受啊!
2013-04-19(原標題)只要有書,我就滿足了/來源:北京青年報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即將來臨,本版謹以此文與所有愛書之人分享-本文選自李偉文《閱讀是最浪漫的教養》(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李偉文
最近這些年,不管到圖書館或書店,看到滿坑滿谷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生動、種類繁多的兒童讀物,內心總是充滿許多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是羡慕現在的孩子有這麼多精彩的書可以看,可是另一方面又很感慨現在的孩子因為影音聲光娛樂太多,很容易失去了安安靜靜進入閱讀世界的機會。
我的童年時代沒有電玩,沒有什麼才藝班、補習班,也沒有什麼好看的電視節目可以打發時間,因此課外書很快就成為排遣寂寞的良伴。
六十年代我讀老松小學,那個時候經濟正從農業慢慢轉型為工業,大部分家庭雖然清苦,但是社會風氣淳樸,也相當具有人情味。還記得拿著玻璃罐到巷口雜貨店“打”花生油的情景,當時家裡買雞蛋都是挑較便宜的破蛋,可是即便生活這麼拮据,父母親還是會省出一點點錢讓我們到位於牯嶺街的舊書攤買書。
當時也正是臺灣人口急劇增加的階段,老松小學學生人數超過一萬人,因為校舍不足,學生只好分為上午班跟下午班共用一間教室,也就是某些班級這星期只要是上午上課,隔周就改成上午放假下午上課,各班輪流著只上半天課。印象中就有許多沒有玩伴的漫長午後等著打發。我們家住在萬華火車站後面大理街的一間小小的兩層小公寓,二樓頂有個斜斜的小閣樓,我常常一個人坐在閣樓窗戶邊看課外書,在安靜閱讀中憧憬著外面的廣大世界。
後來讀中學時,我發現志文新潮文庫出了一本翻譯書《屋頂間的哲學家》,書中貧窮又喜歡看書的主角就是住在這樣的閣樓,也常常像我一樣,邊看書邊看著窗外的芸芸眾生。我非常喜歡這本書,一直到大學,有同學或朋友生日,就送他們這本書當生日禮物,印象中至少送出去好幾十本呢!
小學利用班長特權,到每個同學家做客(其實是為了借書!)
回想我讀小學時,物質還很匱乏,書算是很珍貴稀有的,即便我們到舊書攤買殘缺不全的便宜舊書(真的,當時舊書攤的書不是缺封面就是會掉內頁),買得起的數量還是非常有限,根本填塞不了我的閱讀胃口,當時圖書館很少,藏書其實也不多,距離住家又非常遠,一次也只能借兩本書,往往去一趟圖書館折騰半天借回家,沒多久就看完了,實在划不來。
幸好小學時我功課很好,一直當班長,當年當班長還蠻有威嚴的,於是就利用班長的“權威”與頭銜,到每個同學家做客,同學的家人都很歡迎我,希望他們的孩子能跟我這個好學生在一起。其實,我每次去同學家的主要目的是去看他們家有哪些課外書,然後就花一點時間幫同學把書重新排列,分成兩堆,一邊是我已經看過的,另一邊是我沒有看過的,然後就吩咐那些同學每天帶5本書到學校借我,同時我也將前一天看完的5本書還給他。
等到一個同學家的書全都被我看完了,我再到另外一個同學家做客。就這個樣子,兩年不到,等到全班同學家都去過後,剛好是升年級換新班級時,換了一批新同學,我又可以重新如法炮製,甚至換到其他班的同學也會跟我介紹他們班上的同學,帶我去他們家借書。
初中時慫恿同學買書(其實也是為了我想看書!)
到了中學時,開始流行武俠小說,古龍、金庸的小說一套一套的,我當然買不起,圖書館也借不到(當年圖書館不可能購藏這類的小說),我就慫恿有錢人家的同學去買,好玩的是,有些同學買了之後不敢帶回家,就擺放在我這裡。
當年要借到一本好看的書得費許多心力,哪像現在成堆的好書擺在孩子面前,他們都還不見得願意撥出時間看呢!
高中、大學、當兵就像個吃書的人(看再多書也沒有飽足的一天!)
等到上了高中,建中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因為開放的學風,所以有許多精彩的人物各自追求自己的興趣,從那些同學的涉獵裡,知道自己的不足,也激勵了自己往許多以前未曾接觸的領域去探索,一直到大學,我就像是一個餓壞肚子的人進入吃到飽的餐廳一樣,總嫌肚子不夠大,一方面參加許多社團盡興地玩,一方面又發現世界有那麼多精彩的學問吸引我,只怨恨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夠用。
大學時因為常到圖書館借書還書,跟幾位圖書館小姐混得很熟,她們建議我乾脆當圖書館的工讀生,還有工讀金可以領。那些工讀金就成了我的購書基金,畢業搬離宿舍前,我將所買的數百本課外書全捐回給圖書館,那些工讀金就算是我幫圖書館選購的書費了。
大學畢業後到馬祖服役,運氣不錯,分發到馬祖地區最大的軍醫院當醫官,在軍官宿舍裡有自己的書桌與書架,戒嚴時期,在外島當預官一年只能返台探親一次,除了早晚點名看診及偶爾出操野戰訓練,其實閒置時間非常多,沒有什麼值得操心牽掛的事,或必須煩惱耗費大腦精力的任務,這一年又九個月完完整整的日子,整天看書、看海、看雲,真是一生很難再有的享受啊!
開業後,將診所打造成社區圖書館(終於有買書的正當理由)
退伍回到臺灣,進大醫院工作幾年後自己開業,因為診所空間蠻大的,就打算順便開一個社區圖書館,表面上是可以推廣閱讀,服務社區,但實際上可以解除家裡面滿溢而出的書,解除常常被太太叨念的煩惱,同時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買書。
因為開圖書館,總得有固定預算買新書,不然開業之前每次買書都得偷偷摸摸的,每當老婆念說:“家裡到處都堆滿書了,你還買書!”我只能故作無辜狀說:“我哪有!這本是好久好久以前買的舊書!”
從書海中看到心所嚮往之處=找到人生價值與方向
長大後,買書的錢不是問題後,對於擁有一本書反而沒有太多感覺,記得小時候想買書,就得期待很久,存夠錢才能買到一本屬於自己的書,書拿到手都會興奮得好幾天沒辦法好好睡,會翻來覆去地欣賞。
因為書看得不少,從任何一本書中也或多或少有些收穫,自己的價值觀或觀看世界的方法,也一點一滴地逐漸累積。
我最怕有人問我:“你最喜歡哪一本書?”“哪一本書對你影響最大?”因為我想不起來,也無法指出某幾本書說:“就是它們塑造成今天的我。”
不過倒是有兩本小時候非常喜歡看也一直留在我身邊的童書,冥冥中與我這幾十年的生命歷程相合。一本是《十五少年漂流記》,描述一群少年因意外漂流到小島,一起分工合作解決困境的求生冒險故事。
另一本是《櫻桃園》,水牛出版社發行,內容是英國倫敦四個兄弟姐妹,因為身體虛弱,爸媽就把他們送到鄉下的叔叔家調養身體。他們碰到一個住在山裡的野人,野人帶著這四個小朋友探索自然,獲得許多課本學不到的珍貴知識,也讓身心更強壯了!
不知道是不是《十五少年漂流記》及《櫻桃園》的影響,我嚮往一群好朋友一起冒險,共同努力的情誼,參加童軍團,組織荒野保護協會,帶領孩子走進大自然,不就是這兩本書的主題嗎?
有人說,小說可以讓我們從虛構出來的故事中,尋找到自己真實人生的價值與方向。
當我們喜歡一本小說,崇拜書中的主角或厭惡故事裡的某個角色時,這種愛恨分明的情緒,就在無形中影響與建構我們的價值觀了。
總覺得欠書一份情,推廣閱讀、推薦好書成了義不容辭的使命!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是個好奇也是個愛玩的人,參加許多社團,在不務正業的事務上耗費了許多心力,興趣或關注的主題隨著生命歷程而轉移,但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是我對閱讀的熱情。
閱讀使我們對身處的世界保持“又即又離”“既出世又入世”的態度。因為書,我願意投入紅塵奉獻心力;也因為書,我也可以逃回精神心靈的世界,與世無爭,自得其樂。
我很慶倖從小有機會體會到閱讀的樂趣,從此不管世界如何變化,遭遇幸或不幸的事情,都能保持平靜喜悅之心,因此懷抱著野人獻曝之心,想讓大家也能進入書中美好的世界,因此,這些年我最快樂的事就是擔任各種圖書獎項的評審委員,同時即便再忙再累,只要有機會,也會儘量抽空幫忙推薦各種好書,因為我覺得這一輩子我受益於書太多了,總覺得欠書一份情。
從閱讀中所獲得的快樂,真的遠遠超過這一切人世間一般人所追求的價值。
也因為充分享受到閱讀的樂趣,所以我不在乎物質世界的口腹之欲或名利虛幻的追求(比如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別人對我有什麼看法……),只要每天有幾個小時時間可以在書海裡悠遊,吾願已足。
以前,很難表達出這樣的感受,因此看到作家吳爾芙在《普通讀者》一書中的描述,讓我心有戚戚焉,感動到無法自已:
“……我往往夢見在最後審判那天,那些偉人,那些行善之人,都來領取皇冠、桂冠或永留青史的榮耀等等獎賞的時候,萬能的上帝看見我們腋下夾著書走近,便轉過身,很羡慕地對著聖彼得說:‘等等,這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他。他們一生愛讀書’。”
馬祖預官軍醫 看書、看海、雲,一生難再有享受◎李偉文
- 2013-0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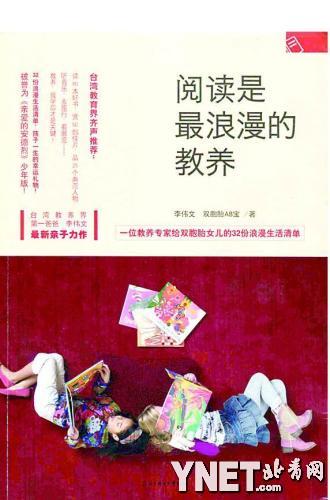
李偉文《閱讀是最浪漫的教養》。(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