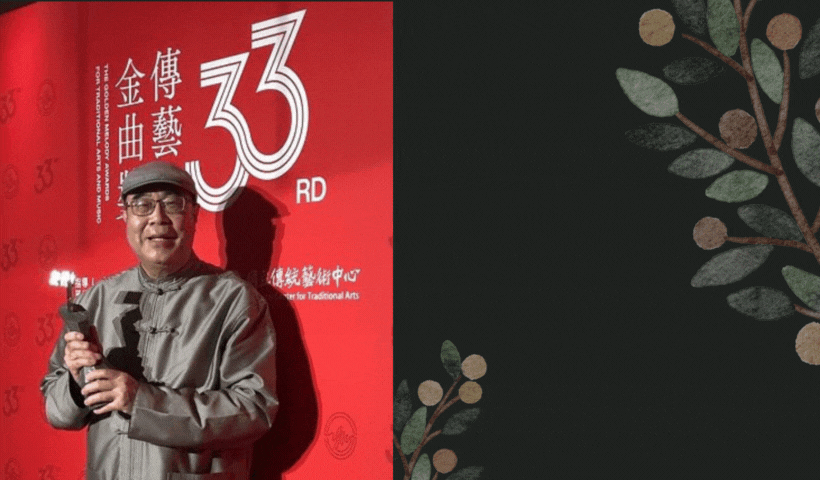2014.02.12【文/桑品載/作家(台南市)】 基隆古蹟碼頭部分面臨拆掉,受文化部邀請,要我以見証人身分,今天到碼頭踏青。
1950年,12歲的我,隨陸軍67軍56師從舟山來台灣,上岸處是基隆第八號碼頭。我記得那天是五月二十日清晨,天氣很好,站在甲板上伴著旭日,看船慢慢進港。
碼頭上,有各中學生組成的歡迎隊伍,學生們揮舞著小國旗,為標示校名的布幔上一式橫寫著「基隆中學」、「基隆女中」等字樣。較布幔稍小的還有歡迎旗幟,上書「歡迎國軍來台」、「反攻大陸」、「殺朱拔毛」等口號。布幔與旗幟都用竹桿撐開豎立,有學生分邊扶持。隊伍後方是鼓號樂隊,演奏的也是學生,各吹各的調,十分熱鬧。
所搭乘的海軍登陸艦,中途奉令作海戰演習,使航程多了一天,約三天後才到。我是漁家小孩,有不暈船的本領,航行中發乾糧,暈船吃不下的便把乾糧給了我,很多人因吃得少、嘔吐而精疲力竭,我倒吃得比任何時候都飽。
或許正因為我精神特好,更因終於到了陌生地台灣,手扶在船舷欄杆,陶醉其中,還高興地向岸上歡迎學生揮手。
終歸我才12歲,沒警覺本在坦克艙內的我那個連已經動身上岸。我是在甲板上看到的,等我發現,再逆向擠回坦克艙,我那個連不在了。
終歸我才12歲,竟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我連長姓蕭,部隊番號一概不知,所以雖問過身旁的人「蕭連長在哪裏」,沒人回答。
我只好夾在其他部隊的人流裏,一起上岸。
船與岸間搭著一塊長方形的木製踏板,走下踏板,有一群婦女分發慰問袋,袋上寫著「反共抗俄婦女聯合總會」印刷字,一人一袋,我也有。比巴掌略大紙袋裏有一塊蛋糕,一個麵包,一根香蕉。
碼頭成「一」字型,兩側各有一個出口,有憲兵持卡賓槍站崗。碼頭外停著許多軍車、上岸的部隊找到了來接他們的車子,井然登車,沒人收留我這個本不屬於他們的小孩子。中午不到,部隊都走了,我還在碼頭上東張西望,不知如何是好。
終歸我才12歲呀,我好怕。部隊離去後,有10多人在掃碼頭,說的是台語,我一句不懂。我穿的不是軍服,像個流浪兒。有人看我一眼,我都害怕會被抓走。
我終於發現有個地方可以藏身——碼頭後方的倉庫。好像每個碼頭都配有一個倉庫,一體的油漆黑,彼此相連,但各有其門。第八號碼頭的第八號倉庫門是虛掩著的,我小心翼翼地溜進去。倉庫很大,放的東西卻不多,都是麻布袋,疊成一落一落。
我靠在一落麻袋上,吃慰問袋裏的東西。
天黑了,倉庫裏只一個大約五十燭光的電燈。我想家,想父母,越想越怕。
忽然,有個憲兵在手電筒光照射下走了進來,很快就發現了我。他問我怎麼會在這裏?我據實報告。他卻怎麼都不信。要我站起來,跟他走。走到出口處,那裏還有一個憲兵,兩人打個商量,檢查了我媽媽給我的布包,裏面有幾個銀元,他們1人拿了1個,然後把我趕出碼頭。
那以後,我流浪基隆成為小叫化子達三個多月,那是後話,不在此贅述。
2009年3月,龍應台正在寫「大江大海1949」,她要去馬祖訪問,約我同行。同行的還有王小棣導演、黃黎明導演和她們的副導演「鐵蛋」。小棣在我赴馬祖前一天,要為我拍上述事情的紀錄片。是日基隆大雨滂沱,除拍攝了我登岸狀況,也拍攝了我此後3個月在中正堂(現為基隆文化中心)前以汊港兩邊草地為家狀況,這部紀錄片,未見王小棣導演做何處理。
基隆碼頭倉庫 藏不住的幼年兵鄉愁…--桑品載(聯合報)
- 2014-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