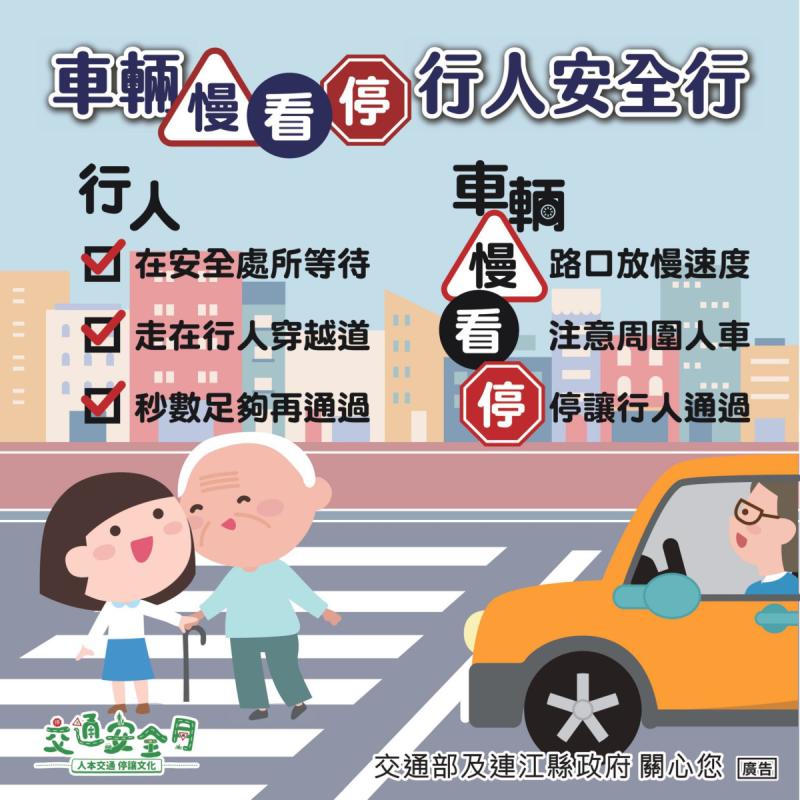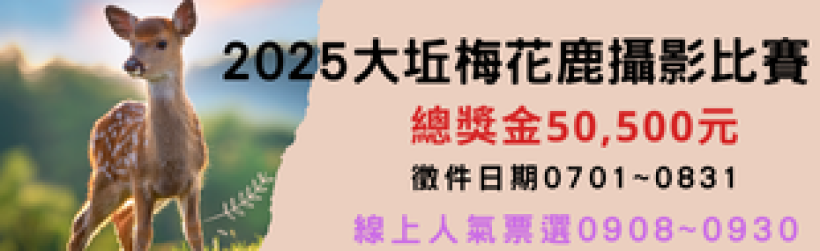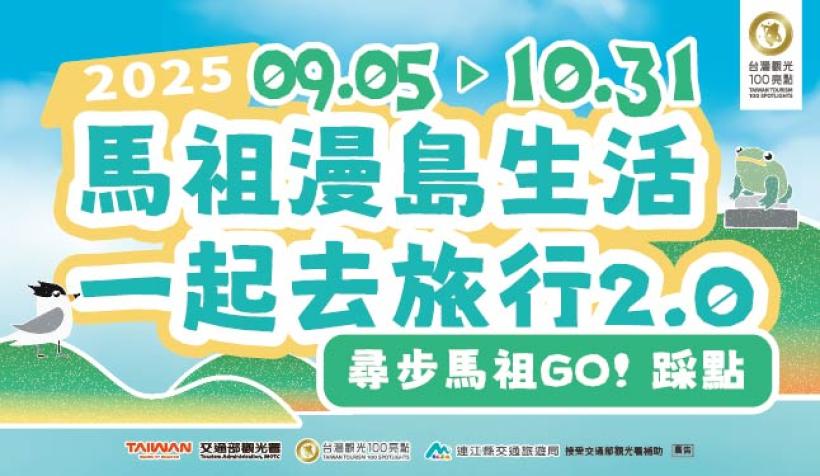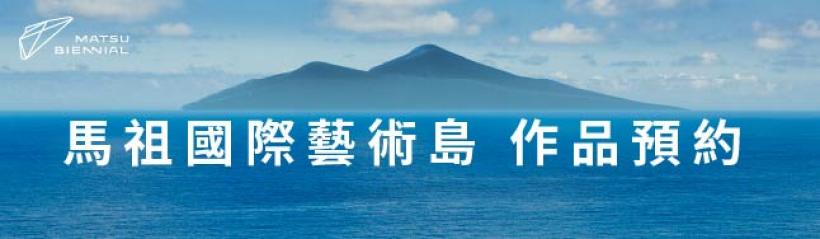(三)丁香魚
鯷魚是近海漁產,馬祖話叫「兜爿(近岸)」。立春以後,東洋水湧入澳前。村人從屋角尋出堆放經年、已經蒙塵的繒網,以薯榔重新染過;繒網曬乾後,陽光下暈著一層暗紅亮光,飽含韌性與張力。泊在岸邊的舢舨,也在叮叮咚咚整修。從鄰村請來的師傅,在石臼內一杵一杵槌搗,混雜石粉、麻網、桐油的塗料,耐心填補舢舨漏水的罅隙。
一個猶有寒意的清晨,天色微明,老代(船老大)早已起身,帝爺案前恭敬捻香,隨後鳴炮,村犬驚嚇遙吠;舢舨入水,開始為期四、五個月的「圍繒」季節,撈捕丁香(即吻仔魚)與鯷魚。
丁香魚季節很短,前後不過個把月。清明前後,薄霧籠罩,海上看不見人影,卻可清晰聽到,澳口傳來搖櫓、拉網的吆喝,悠遠如簫聲。新鮮的丁香魚晶瑩剔透,太陽一曬便融化成水,要立刻加鹽汆燙,馬祖話叫「煠(音:颯)」。煮過的丁香魚有如玉脂,白花花一片鋪在竹箳;經過陽光煨乾,晶瑩剔透、鹹度適當,是魚類珍品。
幼時上學,常趁大人不備,曬場抓一把,一路嚼到學校;講究一點的,花幾個零錢原汁原味夾繼光餅。現在餐館賣的所謂馬祖漢堡,一般都夾蚵仔炒蛋,只能算次品。
馬祖有句俗諺:「十八諸娘囡(女子18歲),就像丁香魺,愈大愈不值錢。」以今觀之,這句話對女性有些不敬。它無非在說,丁香魚長得快,等到透明魚身隱隱現出灰黑內臟,變成「魚魺(台灣稱丁香魚)」,口感帶刺且味苦,就沒什麼行情了。
這時,天氣轉熱,鯷魚陣陣湧至。舢舨不變、繒網不變、漁人也不變,但漁法變了。
(四)鯷囝樹
民國24年出版的《福建省漁業調查報告》紀載:鯷魚有趨光性,性怕熱,喜食浮游生物。
60年代,我在東引教書,補給船泊在南澳碼頭,到了夜間,岸上探照燈打在船艏,為趕潮水清運的士兵照明。同時之際,成千上百的鰮、鯷,瘋狂躍出海面,水花四濺,許多跳到岸上,掙扎翻騰。南澳居民拿臉盆、水桶,大把大把撈撿,人人滿載而歸。
每次搭補給船赴台,船過野柳、金山一帶,通常已是子夜時分,站在甲板上,都可見著明滅閃爍的漁火。後來才知,基隆、金山的漁民,利用魚類趨光性,早已發展出電石、火把、柴油燈的傳統漁法。
軍管時期,島上燈火管制嚴密,禁止漁民夜間捕魚,更遑論以燈光誘捕鯷魚。即使在國軍尚未進駐之前的更早年代,基於電石、柴油等火源取得不易,先民巧妙利用鯷魚趨光性以外的另兩種習性,創發「鯷囝樹」漁法,像艋艚「打楸」一樣,成為馬祖漁業的傳奇。
「鯷囝樹」當然不是真樹。取一條扁擔長度的繩索(竹篾與稻草絞成),一端繫在浮繩上,另一端垂入海中,當作樹幹。樹幹中段織入茅草叢即成樹蔭,遇水散開成傘狀,隨著海流自然飄舞,陽光照射,有若千足之蟲在水中浮游。鯷魚見了,紛紛圍聚樹蔭納涼、覓食,愈聚愈多,萬頭鑽動。過不久,舢舨圍繒悄悄掩至,受驚嚇的魚群掉頭快閃,整批落入網末曩袋之中。
此時,岸上早已籮筐成排、魚販群集,駛往黃岐、梅花的錨纜升帆待發。人們臉上的笑容,就像鯷魚細鱗閃出的微光,映照黃昏的海面,特別明亮顯眼。
(五)鯷魚物語
我曾聽對岸黃岐一位依婆說,她年輕時經常挑「外頭山(馬祖)」「捏鹽」鯷魚,從黃岐走到鶴上販售,穿山越嶺,單程要13個小時。我亦曾在長樂梅花鎮的魚寮,看見人們製作「梅花炊鯷」的技藝。婦人把新鮮的鯷魚,一尾一尾頭尾交叉,整整齊齊,排在竹籃上層;另一位男工提起竹籃吊繩,將竹籃下層浸入滾燙的鹹滷,炊至八分熟立即撈出。竹籃中的鯷魚,像藝術品一樣,晾乾後賣到福州、上海的海鮮市場。
兩岸斷絕之後,鯷魚不再輸往內地,也不可能運到遙遠的台灣,立即面臨「漁獲少,吃不飽;魚獲多,滿地拖」的窘境。島上駐軍雖多,缺乏環境與文化的餵養,不是人人都好此味,部隊菜單極少出現鯷魚。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鯷囝成了島上各家戶夏季餐桌的主角,與番薯飯同時出現。
記得唸小學那幾年,一早到校晨讀,書聲琅琅,小朋友吐氣如「腥」,前後左右全是鯷魚的鮮味。
鯷魚量多價廉,許多人家一次買一、二十斤,剖肚取腸,擱在竹箳上蒸炊,再曬成鯷魚乾。煮槓麵放幾尾可提味,也可炒辣椒下酒。現今山隴獅子市場鼎邊糊人氣店,湯頭極鮮,可以吃到整片的鯷囝乾,老闆娘即是梅花媳婦。
也有人醃漬「鹹配(鹽醃海味配飯)」,一層鯷魚一層粗鹽,層層堆疊封在陶甕內。十天半月後開封,魚肉呈粉紅色,腥鹹逼人。撕一角嚼之,啜一口高粱,耳根立即變紅發熱,有唱閩劇的衝動。
當年物質缺乏,大米、食油尤其珍貴。鯷魚豐收正值端午佳節,母親盛重地將鯷魚裹上地瓜粉油炸,作為祭拜神明、祖先的「碗菜」。於今,鯷魚油炸已幾乎已是料理主流,而我每次吃到,總會無中生有,聞到燃點線香與火燒紙箔的氣味。故鄉的一切,兒時的一切,彷彿都在眼前。
(六)島嶼的底色與滋味
這幾年,馬祖急遽變化,高樓與便利商店愈來愈多,民宿、導遊、餐館、交通,逐漸取代傳統以漁以農的生產方式;也有許多東西愈來愈少,漁寮、艋艚,還有蝦皮、黃魚,已經稀有的讓人無可奈何。
每次聽聞,成群鯷魚驅光跳上堤防,居民爭相撿拾的歡樂場面,暗自欣喜,鯷魚尚未遠去,每年夏至以後,準時回到島嶼四周。但是舢舨、圍繒、鯷囝樹,這些與鯷囝相關的語彙,已漸漸從日常對話淡出;年輕一輩,是否會以迎接藍眼淚的熱情,去迎接鯷囝的週期迴游?
慶幸的是,島嶼仍有數艘漁船晨昏出海,仍有漁人堅持傳統定置網的撈捕作業,他們為島嶼保留夏天的底色與滋味,他們沒有忘記祖先的行業。
鯷魚(下) 文/劉宏文
- 2020-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