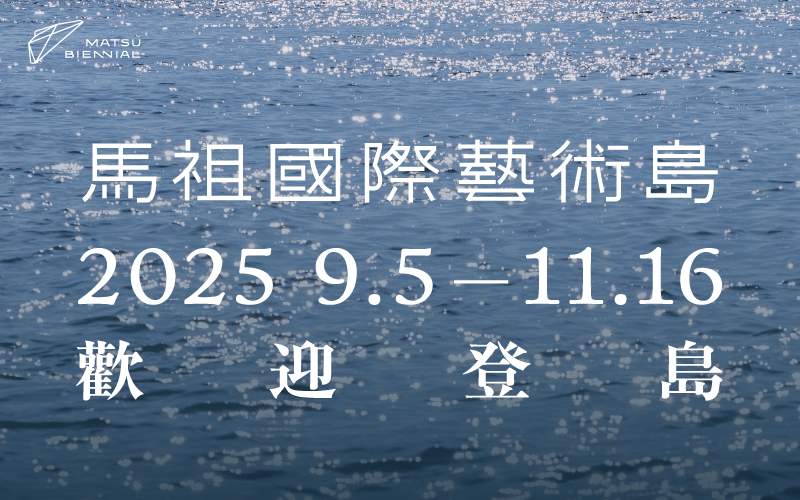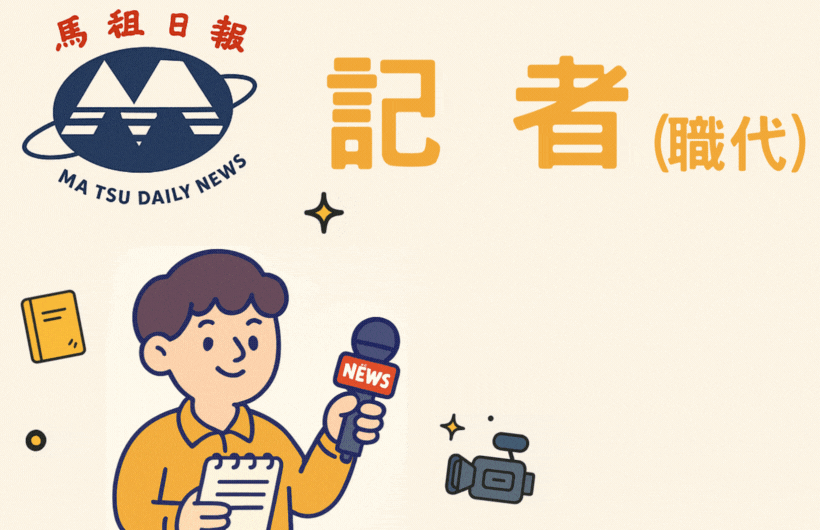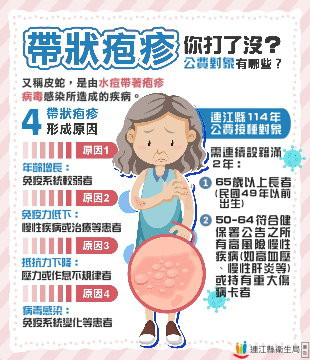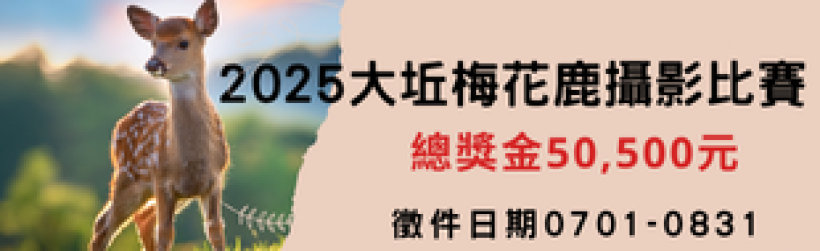(三)
經此鉅變,玉清嫂原已壓制的哮喘再度復發,她終日啼泣,身形更為瘦弱。夜深人靜,她望著熟睡中四歲的依金與未滿一歲的春金,思及留在大陸的長女依梅,今年應該8歲了。
往事歷歷,玉清嫂清楚記得與王木發圓房那年,她16歲,丈夫已經28歲了。那時馬祖人普遍早婚,婆婆告訴她,王木發適婚之齡,因為家貧,無錢付禮金討年歲相當媳婦,她打聽到長樂鶴上有黃姓人家,生女太多,有意送出一個。婆婆以10個銀元,把玉清嫂乞(給)來當童養媳,她來王家才6歲。
王木發長玉清嫂11歲,夫妻有如兄妹,王木發處處護她。圓房第二年即生下長女依梅,玉清嫂產後虛弱得了哮喘,王木發聽人說食「羊老」可療治,借錢買了一頭乳羊,宰殺清楚,塞入陶甕中,淹老酒,敷黃泥封口,以稻米殼煨一天一夜,直到連骨帶肉化成濃汁。玉清嫂食了兩頭羊,病情依舊時好時壞,春暖花開尤其嚴重。
依梅三歲那年,王木發決定帶玉清嫂還有依梅,赴福州「食茶(吃中藥)」。中醫師說,若要根治起碼得服十帖,他們的錢只夠二帖。回程途中依梅口乾,他們跟「大橋頭」旁,一家賣五金的鋪子討水喝,老闆嫂看依梅不哭不鬧,目睭金金,便問可否收為媳婦?玉清嫂當然不捨。王木發見老闆夫婦面容和善,五金鋪子門面堂皇,應該是個好人家;回身看看玉清嫂,乾枯羸弱,回到外頭山不知是否有命存活?
他們終究把依梅留下,帶回另外八帖中藥,還有玉清嫂一路啼嘛的目漬。
(四)
白沙是傳統漁村,「江頭墘(澳口)」常年停泊10多艘大大小小的漁船;有的做(糸孟)捕蝦皮,有的討小海,下網、放釣。王木發家離澳口不遠,春天圍繒捕丁香魚,夏天種鯷魚樹,五月以後放縺捕鯧魚、黃魚和帶魚,玉清嫂晨昏都能看到王木發,油衣短褲,搖舢舨出入兜岸(近海)。
國軍來了之後,兩岸禁絕往來,魚獲銷售通路阻絕,新的行業猶未滋生,在此青黃不接之際,漁民各自摸索生計,適應這個草綠軍服與槍砲彈藥的陌生時代。王木發正值青壯,編入民防隊,又被選為第一伍的伍長。他白天捕魚,夜間揹著村公所發給的一把步槍,站崗巡哨。
此時,兩岸風聲鶴唳,反攻大陸的傳言流竄民間,許多人深信政府即將「抓壯丁」強迫當兵。村裡有一婦人,特地找上王木發,說他獨子「病啞」,不會說話,請王木發轉告上級,免除當兵與民防隊義務。王木發雖知其子只是口語不清、講話含糊,尚未達啞巴地步;但他老實,不忍辜負請託,仍然列冊上告,「病啞」遂不在民防隊徵召之列。
有一日,鄉公所長官來村裡視察,王木發陪同,在澳口碰到「病啞」與他父親,一前一後奮力抬漁網。當兩人開始爬石階,漁網重量壓到後頭,處下坡的「病啞」撐不住,催他父親:「走快一點!」鄉公所長官、指導員、村幹事和王木發,面面相覷,大家清清楚楚聽到這一句。指導員開口:「不是啞吧嗎?怎麼說話了?」
「病啞」不久編入民防隊,搬砲彈、搖舢舨、挖戰壕,還被罰了一個禮拜夜間值哨。他從此懷恨,一切都是王木發從中作祟。
民國39年,韓戰爆發,金門、馬祖成為抵禦赤色洪流的砥柱,「一切為軍事、一切為反攻」,島上駐軍愈來愈多,每隔十天半月,在數艘戰艦護航之下,補給船源源不絕,運來武器彈藥與米糧油鹽等美援物質;相對而言,百姓生活普遍清苦。經常可見部隊在村落附近露天開飯,一群衣著襤褸的老少村人,饞口垂涎,盯著擺在地上的三菜一湯,甚至有人忍不住白米饅頭的誘惑,搶了就跑。
拜美援之賜,每年有二到三次,農復會將美國運來的衣物、麵粉、白米、牛油、包穀粉…等救濟品,分送各島各村。由於粥少僧多,村公所規定小康之家不能領(僅少數),貧戶依窮困級數與家中大小人口,分得不同數量的救濟品;而判定誰家小康、誰家為甲級或乙級貧戶、誰家有幾個大口小口,就是最貼近基層的伍長職責。
王木發是第一伍的伍長,當他向「兩個聲」指導員報告判定結果之時,也同時判定了自己悲慘的命運。
「分救濟」當日,全村莫不引頸期盼。村公所「螺管」響起,各家戶幾乎都來了。有大衣可保暖,有麵粉拍槓麵,有牛油配地瓜飯。衣物按抽籤決定,米糧則秤斤論兩,幾家歡樂幾家愁。救濟品雖然為困窘、逼迫的生活堵上缺口,但也變得錙銖必較,時刻考驗人性的底線。
(五)
那時村公所有位保丁,外號「媳婦仔」,戶口屬王木發管轄。他責怪王木發貧戶判定不公,故意少報他家大口人數,以致少領救濟品。他聽不進王木發解釋,挾怨向指導員檢舉,說王木發經常在夜間偷發無線電訊號。此事被之前與王木發結怨的「病啞」知道了,也跟著起鬨,更變本加厲指控王木發私藏槍枝,以及共產黨宣傳文件。
指導員將王木發涉嫌匪諜一五一十上報汪姓團長,適巧汪團長赴台灣休假,由朱姓副團長接案。他立即派兵進村,將王木發蒙面後,強押到塘岐,關入莿坪一間番仔搭民宅審訊。
王木發驚惶失措,他根本不知什麼無線電、有線電,也沒見過宣傳單,家裡槍枝是民防隊發給,晚上配帶站衛兵。審訊軍官見王木發一問三不知,便將他綑綁門板上,架起來,以扁擔抽打全身。王木發除了回答「沒有」、「不知道」與痛苦哀號之外,其餘無話可供。那朱姓副團長取來電擊器,兩端接到腋下,不斷施以電擊,哀號慘叫的聲音左右鄰居都能聽見。從中午到晚上,王木發叫聲愈來愈弱,終至不再出聲。
那朱姓軍官見王木發已無氣息,慌忙叫人找來繩索,繞在王木發脖頸,佈置成畏罪自盡的假象。他找不到王木發通匪的任何證據,也不可能釋放已躺在地上的王木發,便編寫炮製虛偽的保證書,通知村人作保蓋章,欲掩蓋刑求致死的事實。
數日之後,汪姓團長返馬,問清事情始末,親自帶了白包到王家致意,並且說,要是他未去台休假,一切都不會發生。
除此之外,他們什麼都沒有做。
(六)
歲月艱辛,直到民國80年代,兩岸開放探親,王木發遺留大陸的女兒重新連絡上。姊妹聚首,三人都已華髮叢生。比起青壯之齡早逝的父親,她們此時更為年長。死生契闊,多出的每一吋時光,都在丈量父後的寂寞與淒涼。
民國90年,王木發離世50餘年後,家屬向國防部申冤。在沒有任何文件、任何檔案證據的情況下,曾任白沙村伍長、已遷居台灣多年、年逾80的劉禮泉先生挺身而出,特地由台返馬作證。他清楚記得簽名作保的往事,記得村人往塘岐贖人,見到的卻是冰冷的屍體。他記得每個細節,每個人名,甚至每個人悲憤的臉容。他的每一句證詞,都構成完整事實的基石,沾滿那個時代的淚痕與血跡。
王木發的家人領得一筆遲來的補償,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劉禮泉說:「那有什麼用,他走時那麼年輕,未來的世界何止這些啊!」
《鄉音馬祖專欄》
馬祖人。從小聽炮聲、看大海、住石屋、聞魚腥。及長來台,努力糾正馬祖口音,適應台灣生活。六十初度,仍在追尋、探索;不斷否定、肯定。惟鄉音侃侃,如影隨形,再也壓制不住。
《特別報導》鄉音馬祖/玉清嫂的太平麵(下) 文:劉宏文
- 202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