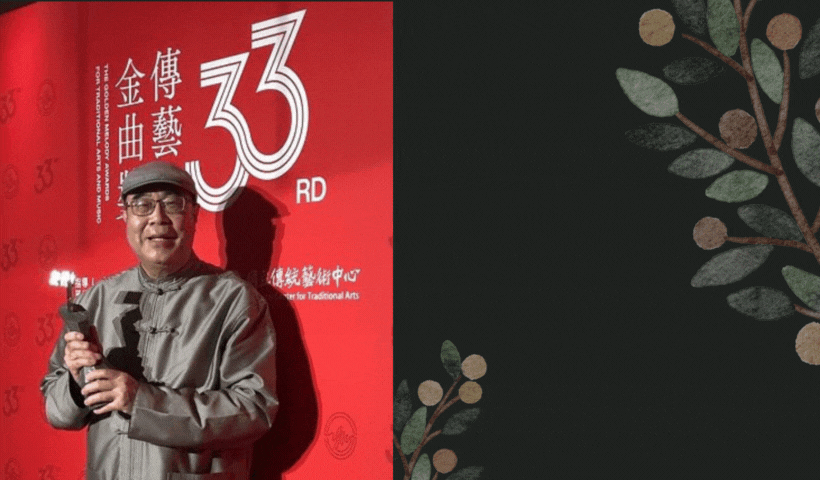消失的地平線
閱讀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1933年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故事從一架英國專機遭到劫持開始。主角康維與三位同伴被迫降落在西藏邊陲,被當地人請入一處與世隔絕的神祕山谷--香格里拉。在這裡,時間彷彿靜止,居民長壽、氣候宜人,人們過著遠離塵囂的寧靜及有現代化設備的生活。修道院裡一位兩百多歲的喇嘛,邀請康維成為繼承者,守護這塊和平淨土。康維內心掙扎。他一方面受到香格里拉精神的吸引,一方面也難以割捨塵世的責任與同伴的呼喚。最終,他選擇離開,卻在途中失憶。多年後,雖然記憶逐漸恢復,但「香格里拉」已如夢般朦朧,只留下「消失的地平線」作為他靈魂深處的牽引。
瀘沽湖的「湖水綠」及溫柔,
就是我的香格里拉
島居生活一半詩意;一半困頓。趁著夏天假期到心中嚮往的雲南及香格里拉去看看,查了一下旅遊資料,擔心自己會有高原反應,數年前只是到海拔2610公尺玉山登山口便上氣不接下氣。熟識的領隊鼓勵我不必擔心,八天行程中一天登高一點,就會慢慢適應,於是想要出走的心立馬跟上了。
第一天夜宿雲南的「楚雄」,海拔不到2000,這是適應高海拔的第一站,第二天一早年輕的導遊問:「昨晚一覺到天亮的請舉手?」只有五個人舉手,我是其中之一人,正感到驕傲,導遊繼續說,你們五人是高山症的高危險群,我緊張了起來,坐在旁邊的同窗好友馬上調侃說:「妳在家不也是一覺到天亮!」
旅程中最舒服的是氣候,除了感受紫外線較強外,高原氣候不流汗濕黏且涼爽。瀘沽湖在雲南和四川交接點,我們遊湖乘坐的小船由摩梭族阿哥、阿妹划船搖槳,載我們到對面的里務比島再折返,我坐在搖櫓的阿妹身旁,這樣勞動下已中年的阿妹皮膚黝黑、眼笑成縫,划槳如舞,每一寸的肌膚都緊實。我一直找她說話,想多了解他們的生活,她說瀘沽湖畔是摩梭人的自治區,摩梭人走婚受道德約束,你情我願卻不受婚姻束縛,且白首到老。她的友善是一種瀘沽湖的「湖水綠」,溫溫的中間綠色,搭配冷色系的藍天呈現寧靜的感覺,她的開朗與韌性,正如這片湖水,溫柔卻有力量。
第二天清晨起個大早,在瀘沽湖旅人還未醒時,到瀘沽湖旁散步,你無法只是用「湖光山色」來形容這裡的美,我們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到了瀘沽湖,湖邊散步輕快悠閒,身旁一叢薔薇,因高原日照強花色艷麗,突然羨慕起這叢薔薇,幸福的薔薇,日日與瀘沽湖相伴。一位摩梭人女性長者,從湖對面的「摩梭園」裡走出來,口中誦著梵音,在湖邊刷成白色土爐裡焚燒二葉松,接著右手持轉經筒,左手持念珠,繞著白色土爐轉圈念著經文,我也雙手合十跟她繞圈,心裡默念著:祈願家人都健康平安。幾圈之後,長者發現我跟著她,便用普通話說:「心裡想著好事,就會平安。」可不是嗎?
清晨薄霧籠罩,宛若仙境,整面湖靜謐而空靈,遠離塵囂,讓人彷彿置身世外桃源。啊!這裡就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了。
在旅途中修行
在旅途中保有一雙看世界的眼,也對服務我們的人們懷著感謝。同團中有人搶菜卻吃不完;有人一路高談,沒有當下;急著自拍,不見風景;有人嫌冷氣不夠冷、水果不甜。我耐住性子說:「我們台灣的精緻農業發達,每一樣水果都很甜,真是寶島呀。」那些瑣碎,我只能提醒自己,不要成?他人眼中「憎厭」的樣子。
前往4449米的香格里拉,肅穆的「松贊林寺」,雖遊客如織,但旅人打心底的敬拜,一切仍顯莊嚴,在這裡有輕微的高原反應,頭昏、耳鳴、心兒碰碰跳,讓一切都顯得虛虛實實,增加了神祕感,也有如《消失的地平線》裡遠方的故事。旅遊行程要結束時,「薇帕」颱風來臨,打亂了班機,這趟雲南行多兩天的行程,我享受著如無工作般的「不急」,而「不急」就「不累」。在旅行中修行,是一件好事。
消失的地平線,在我們心中
回到小島,繼續閱讀《消失的地平線》,腦海裡常常浮現廣闊的草原、連綿不絕的高山;流水滔滔的金沙江;藍月谷令人難以置信的湛藍湖水;洱海邊的一大片有靈氣的象草,吸吐間仿彿還能感受高原乾燥稀薄的空氣。
再讀此書,就像走入一場關於時間、記憶與靈魂的對話。地平線若是畫分天與地之間的線,那天堂來到了人間,地平線就會消失,故事的核心是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可能就隱藏著天堂,如果不向外尋求寧靜、祥和與安逸;而是當品一口咖啡、享受一縷陽光或一陣清風時,也能獲得內心平靜,或許就找到自己的「香格里拉」了。
這不只是一個關於遠方的故事,而是在詢問我們:在這紛亂的時代裡,我們是否還能保有內在的寧靜、祥和及安逸?還有是否願意在庸碌的日子裡仍然有詩意?
島居隨筆 之七/文:陳翠玲
- 2025-08-18

搖櫓的阿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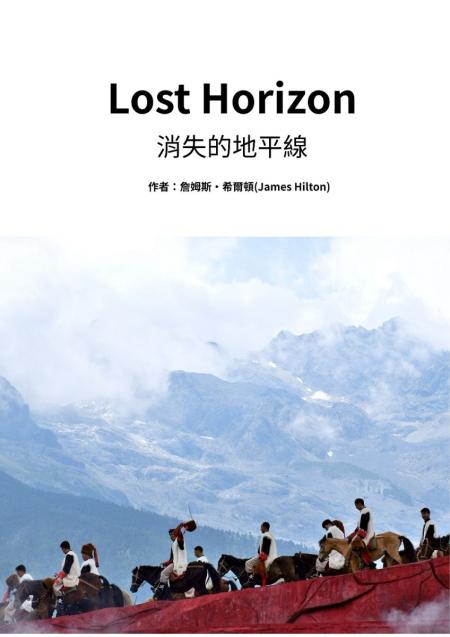
《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

摩梭族長者。